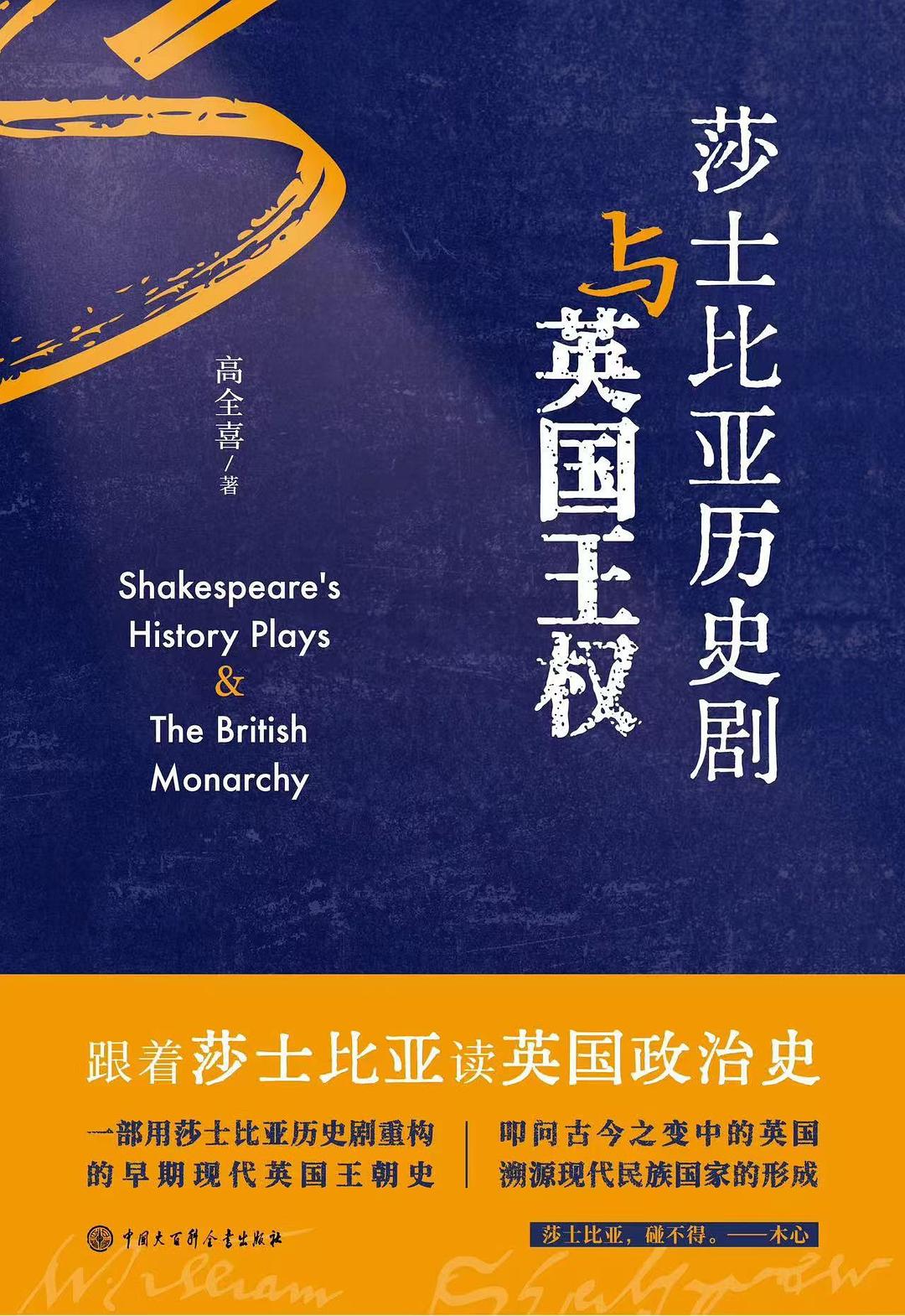
《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高全喜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4年8月版
戏剧能否真实反映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繁复的英国政体演变?文学何以处理都铎王朝政教之争或玫瑰战争这样既具体而微又宏大叙事的历史大变局?莎士比亚是不是足以理解并对质马基雅维利主义与彼时的神学政治论?熟识西方早期现代政史的读者也许会生发出相关的疑问。另一方面,通读莎士比亚文本及其学术史,或者了解诸如施特劳斯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阿兰·布鲁姆论域的读者,则将反过来思考,政治哲学或思想史的路向甚至于历史剧、英国剧的概括会不会狭隘化了莎士比亚的经典意义?毕竟,根据诸如哈罗德·戈达德(《莎士比亚的意义》)、哈罗德·布鲁姆等学者的分析,莎士比亚的意义正在于其覆盖并超越了四百年来的历史哲学、政治史学、启蒙精神、浪漫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东方主义、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等任何单一史学、政治学、哲学、文学角度的理论与研究的范畴。
人们常说莎士比亚、歌德的作品属于全时代与全世界,但如果以此套语草草带过,以期替代或忽略细读的努力、智识的辩驳、语境的解析,那么恐怕作为真言的套语终将会沦为空话,精准的判断会近于武断。就莎士比亚文本而言,中文学界的探索依然方兴未艾,莎士比亚仍是有待译介、注疏并从文本内部与外部相结合以进行研读的世界文学典籍。而宪政、法权与史观方面的路数尤为重要,因为这一方向可以回答上述的疑问,说明经典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细密缝合,补益文学热爱者对杰作背后客观环境的直接认知,为法学、史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提供视域上的拓展,提供与国际莎学界或西方早期现代政治研究界平等对话的最初的可能性。
高全喜教授的新著《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4年版)正是在这一多学科发展逐渐走向精深化并艰难寻求科际整合的中国当代人文学术境遇下应运而生的。在欧美尤其是英语学界,从莎学界出发或由政治哲学与思想史领域开端并与对方形成交相呼应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政治剧、英国剧研究已然颇具传统。由此译介进入中文世界的专著也十分值得关注,比如华夏出版社“经典与解释·莎士比亚绎读”所带来的蒂利亚德《莎士比亚的历史剧》、阿格尼斯·赫勒《脱节的时代:作为历史哲人的莎士比亚》、阿鲁里斯和苏利文编《莎士比亚的政治盛典》、保罗·坎脱《莎士比亚的罗马:共和国与帝国》等,这一派是专门从政治哲学和政治史学切入文学研究的。又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图书出品方的“莎士比亚研究”丛书,其中包括了内外兼修的三种莎学著论,即专著、注疏与译介,分别如张沛《莎士比亚、乌托邦与革命》、徐嘉笺注《〈麦克白〉注疏》、马里奥特《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英国史》等。事实上,国内专门研究莎士比亚如罗马剧或英国剧等著作已有令人可喜之建树,但综合了以上中外成果并形成系统性研究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中国专著,《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也许是头一部。
高全喜教授向擅跨界精研,《浮士德精神》《画与真》《独自叩问》等皆反映了作者在专业的法学、政治学、哲学、思想史等学科之外宽广的文学与艺术研究兴趣。而在《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中,作者在莎士比亚文学场域中充分发挥了个人的专业性优势,为社科与人文的、西学中文史哲的跨越,搭建了精准沟通的桥梁,同时也直接证明了: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之间,或者说莎士比亚文学与政法、历史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高明而错综编织的关系。作者显明了莎士比亚文本中内隐属己的君主论、都铎神话、英国情结、人文理想。《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并未将论域的界限划分在莎士比亚英国剧之中,而是通过三大部分首先定义“何为莎士比亚历史剧”,然后细读存有阐释之循环含义的诸多莎剧,最终托出“英国王权演化”的内在理路,而这一理路早已被莎士比亚或有意或天才地先觉把握在了他不朽的剧作脉络之中。
顺着作者的思路,我们不妨将作者所论述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概括为内篇、外篇与杂篇。内篇较好理解,即作者在第一部分概括的“历史中的英国:十部英国历史剧”。从历史上王朝本身的善变演绎而论,莎士比亚英国剧中的国王当然以约翰王(1119-1216)为始而以前朝亨利八世(1509-1547)诞下曾为莎翁之今圣的伊丽莎白(1558-1603)为终。等到莎士比亚与人合作《亨利八世》(1612)之际,都铎王朝已然由斯图亚特王朝所鼎革(1603)九年之久。然而《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的论述逻辑却与莎士比亚本人撰写英国历史剧的展开逻辑相平行,而与历史发生时间有所不同,这尤其体现在莎士比亚的第一四联剧和第二四联剧之上。莎士比亚第一四联剧由《亨利六世》(上、中、下)和《理查三世》所构成,第二四联剧则由《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亨利五世》所构成。玫瑰战争后发之事创作在先,而“中世纪的两个身体”与“空王冠”等前朝梦忆则意犹未尽、撰写在后。莎士比亚每部剧的创作顺序也如他每部剧中的每一字句那样是有精心设计的,这可反映他在具体修辞、排布与虚构之外,对于政治尤其是英国王权的深刻思考。
比如从哈尔王子到亨利五世的亨利·兰开斯特。《亨利五世》(1599)一剧为莎士比亚集中创作历史剧时期的收官之作,亨利五世这一人物形象也早在第二四联剧的前三部剧中进行了集中的铺垫。简而言之,亨利·兰开斯特作为莎翁十年英国历史剧生涯的最终君主的样子,决定了历史剧中英国政制的样态、莎士比亚心里理想君王的面貌(或相反)、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艺术中对民族国家和王权正当性的人文判断等等。兹事体大,列奥·施特劳斯谓作者常在文本最中间部分插入自己的核心思想,《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在全文三部分的中间部分、第二部分五章中的第三章“国王的成长史”中对以哈尔为中心、以亨利四世和福斯塔夫两位“精神父亲”为辅助集中处理当哈尔称为亨利五世的养成研究,可以说是把握到了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图穷匕见之秘。关键还在于为什么要以文学家莎士比亚之眼来看待或应处于政法视野下的英国王权相关问题?熟稔于政法学的作者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认为莎士比亚:
试图构建他的理想主义的既具有现代早期意义又秉有古典德行政治的明君——英格兰新君主论。这从表面上看还是属于都铎神话的历史叙事,很多评论家依此把莎士比亚纳入都铎历史观念的谱系之中。但正像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所指出的,莎士比亚并不真正属于这个系列的文学编撰者,更不是都铎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打造者,而是有着自己的独创性思想,很多话语俱在不言中矣。当然,这里有莎士比亚稻粱谋的处世之道,不过,他并非反对都铎神话的历史叙事,而是不满足于此,试图超越其历史的狭隘性。(《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第122页)
亨利五世究竟是莎士比亚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强有力回应还是戏仿性反讽,历来众说纷纭,还有待商榷。但高全喜以专业视角解析了莎士比亚式都铎史观、辉格史观、宪政史观三而一的超越性,则无疑是精准把握了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永恒价值。有趣的是,莎士比亚的永恒价值首先体现在他对当下情境的深刻反映与反省。莎士比亚自然并不会以政治学家和史学家的观念写作他的历史剧,早中期生活于都铎王朝中的他对宪政史观的认识无疑更为抽离。这以上条件都不构成对莎士比亚认知现实与英国的障碍,反而为出身于早期现代的他提供了万事俱备、可供运用的素材及思想。任意调动比如《亨利五世》中第一幕第一场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亨利王辨析入侵法国的合法性问题,或者第二幕第二场中亨利假借叛国罪处死剑桥伯爵的诡辩修辞和演说术桥段,即可发掘莎士比亚对政治统治中似是而非的权利和权力辩证法、王朝更替后历史遗留因子的草蛇灰线式的多层次铺垫与揭露。只有足够矛盾与复杂,虚构才能比现实更加真实,让现实中最为荒诞但常见的政治风云于戏剧中得到瞬间的凝固和表征。
让我们再来看看“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外篇与杂篇,作者将其概括为“想象中的英国:其他王国剧与罗马剧”。根据第一部分的概述与第二部分的演绎,我们且将外篇对应于“权力的:《哈姆雷特》《麦克白》与《李尔王》,杂篇对等于“共和理想:《尤利乌斯·凯撒》及其他罗马剧”,这便是作者广义上的“莎士比亚历史剧”:
莎翁的历史剧除了狭义的十部英国历史剧之外,还包括另外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以英格兰王国周边其他王国的历史与政治演绎为主题的历史和王朝剧,例如发生在丹麦王国的《哈姆雷特》、苏格兰王国的《麦克白》、不列颠王国的《李尔王》等,这些构成了莎士比亚历史剧的空间结构的扩展;另外一个便是莎士比亚创作的罗马剧,例如《科利奥兰纳斯》和《尤利乌斯·凯撒》《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它们构成了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的时间结构的溯源,把英国政制及其王权演变上溯到古典罗马时代政制巨变的大背景下予以审视。总的来说,通观莎士比亚历史剧,其实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别,若把它们叠加整合在一起,可以更为清晰和深刻地了解莎士比亚关于政治体制、战争情势、君主德能以及文明演进、人性幽暗等多个维度的思考和戏剧化展示。(《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第321-322页)
如此看来,外篇为横向空间轴而杂篇为纵向时间轴,在更纵深的莎士比亚历史剧坐标系中,莎士比亚的文学与政法、历史的交错编织才能得到整全的比较与考量。作者通过这部新著想要解读的,正是介于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之间的莎士比亚如何以将天才的原创和语境的错杂结合在一起,交托出莎翁属己的理想英国政制情结甚或更具有人文主义底蕴的政治人性的剖析。
以《麦克白》为例,《麦克白》和《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以莎翁四大悲剧名世,作者却将前三部以“权力的游戏”为统一单位将其置入历史剧名目里,点出了历史剧与王权紧密联系的主题。其中《麦克白》以“麦克白夫妇的野心”贯彻全剧,突显了“权力的诱惑”,作者开门见山:“麦克白的悲剧是王朝政治中触及王权最核心的一幕政治悲剧”,“因为这部悲剧与人性和政治有关,它以戏剧的方式把人类生活的最核心内容即权力欲望及其悲剧性的结果赤裸裸地展示出来。”(《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第336页)《麦克白》虽以古苏格兰王国为背景,但我们将察觉,莎士比亚始终在映射着英格兰王国自身的政权命运。从这一意义来看,我们也将更好地理解为何作者称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展现了两个悲剧:权利野心的悲剧和权力本身的悲剧。之所以称《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为文学、政法与历史的“错综编织”,其理由亦可作如是观,该书与莎剧整体还有单部剧作如《麦克白》都以各自及相互纷繁交织为特点,并且在纵横交叉中甚至设置有意为之的“错觉”,像莎士比亚对时代和地点的“误置”,像高全喜对“悲剧”“政治剧”“历史剧”等后天固化题目的交错布局,像二者都认识到的批评权力本身不意味文艺复兴前后一度流行的权力虚无主义等等,都避免了单调同质又描摹了现实本身复杂的纹理。
细心的读者还可在作者提示的细读与互文中挖掘出莎士比亚自己有意为之的暗线,此处仅举两条作为佐证。第一条是《麦克白》苏格兰国王邓肯的篡位事件。莎剧多沿袭“古已有之”的历史和文学题材,《麦克白》的故事背景也有史可考。但莎士比亚能做到“倒行逆施”,是为大手笔,《麦克白》的要点之一就在于删去了麦克白本人的王位合法继承权。根据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在《编年史》(Chronicles)中的记载,“按照王国旧法,若是王子年幼无法掌权,最近的血亲将继承王位”(转引自徐嘉笺注《〈麦克白〉注疏》引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2页)。莎翁弱化了王权继承法、邓肯羸弱统治、麦克白统治高效等史实语境,还将谋害篡位事件在第一幕便交代完毕,使得故事本身更加鲜明化了这部“政治悲剧”的残忍与幽暗。况且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恩怨关系直到莎士比亚时代也从未停歇,这便直接指向了英格兰的国际关系甚至内部鼎革历史的血亲、人伦、政教、权势矛盾。我们从作者的另一部著作《苏格兰道德哲学十讲》(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版)前两章中会理解到背后更为深远的古今剧变。
第二条暗线埋在《麦克白》第四幕第一场麦克白于山洞里见众女巫的惊怖场景之内。兑现了女巫预言、早已攫取了王权的麦克白饱受着良知、怀疑和不安定的境况的折磨,只身奔赴黑暗宴会,妄图寻求能让自我得到安稳的、究竟到底的吉兆。在虚与委蛇中,女巫带来了一出戏中戏——“八王秀”(a show of eight kings):苏格兰的八位国王轮番出场,其中缺少了一位女王——苏格兰的玛丽一世。玛丽已在莎翁创作本剧(1606)的十几年前被伊丽莎白女王处死(1587)。与此同时,麦克白惊呼第八位国王太像他已秘密谋害的班柯,而班柯的后代根据女巫最初的预言是将要成为苏格兰国王的。更要紧的是,不论是班柯还是当朝圣上詹姆斯一世,他们都属于斯图亚特家族。在三年前也就是1603年,莎士比亚和他的英格兰经历了都铎王朝到斯图亚特王朝的改朝换代,该如何处理或不处理曾经保护他的伊丽莎白一世及同样接受他的詹姆斯国王强相关的历史背景将决定莎士比亚随后的个人命运。在对血统和政统的触及中,莎士比亚选择了隐晦其辞,他没有避而不写,而是突出了班柯及其后裔的地位,弱化但却没有贬低伊丽莎白的处决行为。并且,莎士比亚这次没有也从来未曾有过对独一王朝或血脉的吹捧或谄媚处理,在赞誉英格兰王国的从古至今的前进历程中,莎士比亚始终与历史编纂和意识形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才能够思考到权力与淫欲之间的阴暗关系,哈罗德·戈达德曾经在《莎士比亚的意义》中展布过这一联系,而高全喜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则将《麦克白》作为权力游戏的典型,再次点出“权力是最毒且能致死的春药,这是莎士比亚对于权力或王权的反省”(第355页)。早在莎士比亚早期的长诗《卢克丽丝遭强暴记》中,莎士比亚就以罗马王国的晚期史实塔克文家族作为素材,暴露了权力的淫威;这一次,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在批判的同时,还由此“开辟了现代宪政主义限制王权专制的思想之先锋”(《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第358页)。莎士比亚对政权和历史的认知与剖析在悲剧中达到了新的成熟的高度,《麦克白》是悲剧,也无疑是政治悲剧和历史剧。
可以发现,作者将近年来流行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政治剧研究成果一并参考在内,包括较为前沿或受到关注的如阿格尼斯·赫勒、玛莎·努斯鲍姆、马里奥特、蒂利亚德、彭磊等人的论著。但同时,作者又提出了不同于以上诸家评析中的某些观念如中世纪宇宙观、政治神学观、阶级分立观、古典主义观、新历史主义观等等,而是在宏观莎翁政治理念与细读文本褶皱并兼的前提下,揭示莎士比亚具体而微的历史演进论,认为莎士比亚“有一个从‘君权神授’到‘能者为王’再到‘王者尊崇’的王权演变逻辑,这个戏剧化的逻辑又与真实客观的英格兰封建王权史大体一致,实现了某种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结合。”(《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第566页)这前可瞻莎士比亚对英国乃至古罗马与古希腊的系列历史观,后可顾莎士比亚蕴藉已久甚至于有意无意中预示了来日的宪政观。
关于莎士比亚如何看待或会如何思考凯撒精神、民主制度、必要之恶、新教伦理、市民社会、古今之变、意大利情愫等等,我们还有许多必须讨论甚至与作者商榷的关键问题等待研究。但作者充分我们证明了莎士比亚如何看以及如何写历史与王权的举足轻重的巨大意义,并且同样重要的是,作者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与全的莎剧阐释循环、细读文本与考辨语境、出乎政法史与入乎文学史也许是揭示和理解伟大经典特别是作为世界文学明珠莎士比亚的唯一法门。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