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教学用书》几乎是基础教育界每一位教师开展课堂教学的重要参考书。近年来,笔者因为撰写《统编语文教材与文本解读》的系列论著,翻遍了语文学科各年段与教科书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在获得不少启发的同时,也对其中出现的诸多解读失误问题甚为担虑。即使有些失误在重印时得到了修订,但如果新教材篇目调整不大的话,教师大多没有自觉意识去使用修订了的《教师教学用书》,于是那些存在的问题,在教学实际中依然得不到及时纠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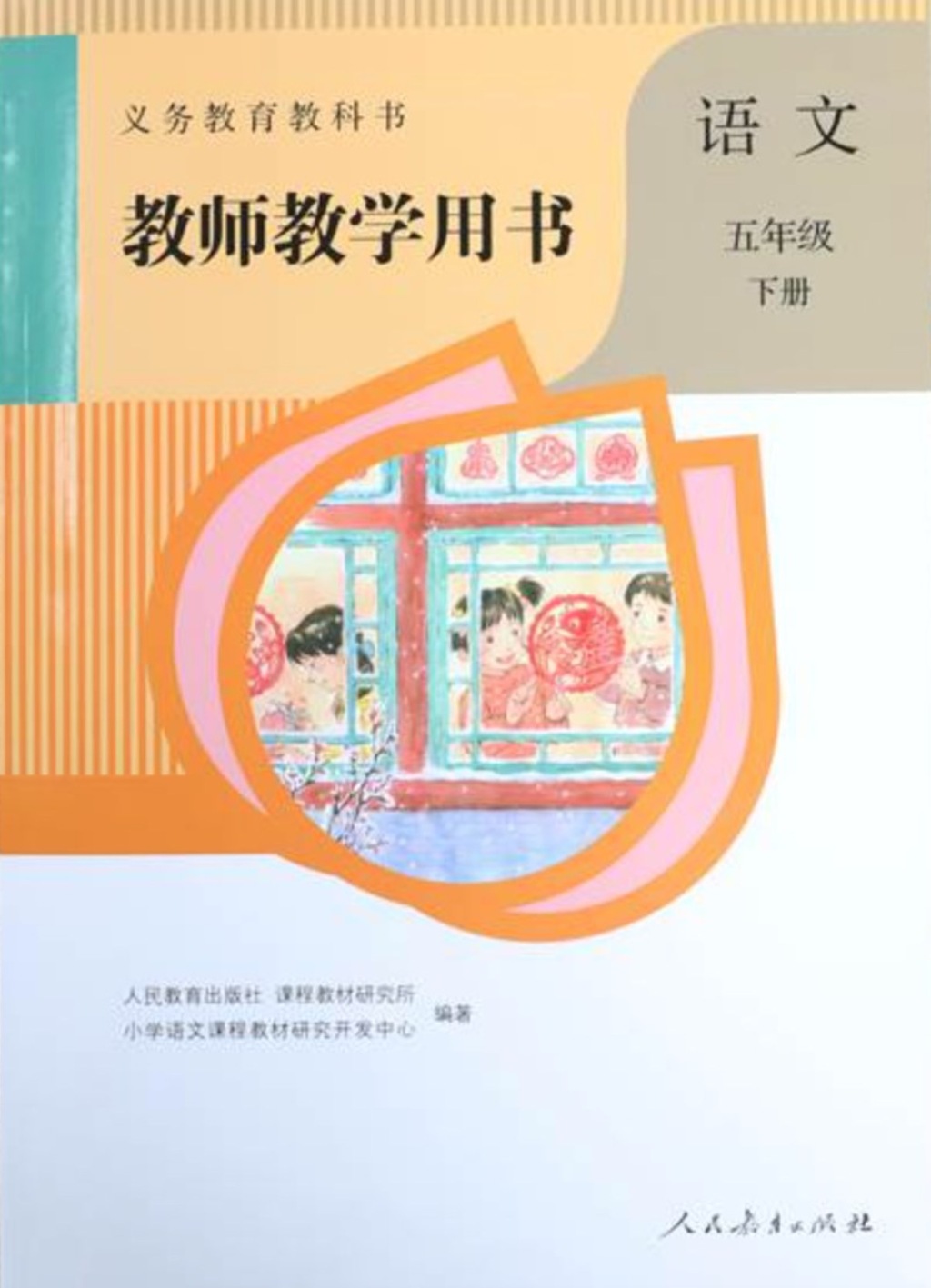
《教师教学用书》,2019年12月版
对于《教师教学用书》解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笔者撰写的《统编语文教材与文本解读》“小学卷”“初中卷”和“高中卷”都有较为深入的分析,为引起一线语文教师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以免以讹传讹误人子弟,这里特撰文予以强调。根据语文学科涉及的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个方面各举一例加以说明。
先看语法问题。
《教师教学用书》的有些编写者,似乎对长句和短句的理解比较混乱,草率落笔,从而带来解读的误导。比如关于散文家吴伯萧的《灯笼》一文,对于其语言特点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但这个判断又是很值得商榷的。其分析道:
多是短句,很少有长句,如“岁梢寒夜,玩火玩灯,除夕燃滴滴金,放焰火,是孩子群里少有例外的事”,“坡野里想起跳跳的磷火,村边社戏台下想起闹嚷嚷的观众,花生篮,冰糖葫芦;台上的小丑,花脸,《司马懿探山》”等,都包含了许多三四字的短句。散文的语言表达与情感抒发息息相关,短句多,一方面显出语言的简净,另一方面还表明抒情的节制、含蓄。但是简洁不等于简单,课文中的诸多短句都是值得吟味的,朗读起来既有语言声韵之美,又有深厚的意味和情味。
细究起来,《教师教学用书》判断《灯笼》一文短句多,长句少所举的例子,主要集中于课文的第1、第2自然段,而整篇课文有12个自然段,每一段中的句子长短形态与其他段落之间,并不构成相似的均质分布的样态。就整篇来看,每段语句的构成,是根据内容表现的需要,写成长短不一的句子。而从通常意义上说,因为篇章的开头部分和主体部分,有着概括和展开的差异,所以,开头部分句子的长短特征,往往并不能说明整篇的语言特征,甚至显示出相反性,也是非常可能的。
“多是短句,很少用长句”这一判断的错误还不仅仅在于用开头部分的例子涵盖了全篇,关键是,分析者自身并不清楚语法意义上的关于短句和长句的定义,所以,其举出的所谓“短句”,大多不是句子,不过是一个长句中的短语成分而已。可以说,写《教师教学用书》的人正好把话给说反了。比如其第1段举出的“岁梢寒夜,玩火玩灯,除夕燃滴滴金,放焰火,是孩子群里少有例外的事”这个例句,其中,前面相对比较短的词语“岁梢寒夜,玩火玩灯,除夕燃滴滴金,放焰火”,都是作为一个长句中的短语成分,来充当后面“是”一字的主语的。即便退一步说,组成主语的那些短语算是他所谓的“短句”,也不是为了表明“抒情的节制、含蓄”,恰是为了表明其抒情的直白,是作家要一口气都把这些内容讲出来,以表明孩子对这些活动的奔赴、兴高采烈的喜欢心情、那种向往的并无例外。总之,《教师教学用书》有关《灯笼》语言特点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每一层意思都说错、说反了。
再举一个对修辞分析失误的例子。
初中语文教材收入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结尾是:
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教师教学用书》对这个结尾的解读是:
“状元宰相”指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客及其御用文人。“地底下”指当时处于地下斗争状态的群众革命力量。这句话是说,中国人是否有自信力,不要看那些反动文人发表出来的文章,而要去看那些真正的堪称中国脊梁的人的所作所为。
如果说,《教师教学用书》以为“状元宰相”直接指“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御用文人”还勉强可通(笔者在“可通”前加“勉强”,是因为鲁迅这里其实用了借代手法,来指代自古以来的一切正统者,当然也包括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御用文人,出于现实针对性的考虑,“教师用书”这么说也可以,但也不应忽视其对自古以来的涵盖性),那么认为“地底下”指“当时处于地下斗争状态的革命群众”,把“地底下”转换成“地下斗争状态”,显然就变得机械和教条了,撰写者大概是《潜伏》一类的谍战片看多了,才会有这种近乎荒唐的分析。这样的理解,已经抽离了鲁迅笔下的具体语境,抽离了鲁迅提及的与“公开的文字”建构出的一组对应的本质关系,即与“公开的文字”相呼应 ,与之相对的“地底下”主要是指没有形诸文字,或者起码是不见于正统的官方记录的文字的那部分人和他们的行为。
最后我们来看逻辑方面的问题。
教材中收入的臧克家的《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主要从闻一多的古典学者和民主战士(臧克家所谓的“革命家”)两方面,写出了他的踏实品格和大无畏革命精神。而教材为引导学生整体把握课文结合和内容,设计了如下的思考题:
闻一多作为学者的“说”和“做”,与作为民主战士的“说”和“做”有哪些不同?彼此有无关联?试根据课文内容做简要分析。
对此,《教师教学用书》给出的参考答案是:
作为学者的闻一多潜心学术,是“做了再说,做了不说”;作为民主战士的闻一多敢于为人民讲话,对敌人无所畏惧,是“说了就做”。这反映了闻一多对社会认识的变化,以及对不同道路的选择。他的“说”和“做”相互贯通,正是他作为一名卓越的学者、伟大的治国者、大勇的志士的体现。
对于给出这样的参考答案,就是从基本的答题要求来说也是不符合的。因为题目要求的是分析,而答案文字给出的主要内容就是信息筛选和梳理。如果把题目要求的“不同”和“关联”从逻辑思维要求的概念界定角度来展开分析,就能说得明白一点。
从闻一多个人角度看,他作为学者的“做了再说,做了不说”,其实是传统文人“敏于事而慎于言”的踏实为人的体现,其中的“说”,或多或少有一种标榜、夸耀、夸夸其谈的意味。而作为民主战士的“说了”,以及“说了就做”,跟作为学者的夸夸其谈的“说”,已经不是同一个概念,而是一种鲜明的政治立场的表态。不对这基本概念予以辨析区分,谈所谓的“不同”,只能是停留于文本表面的简单梳理。此外,从社会交往角度看,作为学者的“做了不说”,就是固守在书斋里,默默工作而不向他人去夸耀。而作为民主战士的“说了就做”,是书斋转向会场、广场,着力向他人去言说、去劝说。这样,“说和做”的概念在闻一多前后两个身份转换中,也发生了意义的翻转。当作为学者的他在开展学术研究而“做”时,他其实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说”,而当他作为民主战士去向广大民众“说”时,就具有了鼓动、组织民众起来反抗的实践意义,“说”反而成了“做”。那么,前后的关联性又在哪里呢?《教师教学用书》提到的所谓贯通,是用“卓越”“伟大”以及“大勇”这些概念来呼应的,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些只是正确的废话。这里贯通的关键是,当他作为学者来进行“做了不说”的研究时,他是从文化层面“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臧克家文章中的文字),这是一种文化理论的革命者,而当他作为民主战士“说了就做”时,就成为社会实践的革命者,这样,从文化理论到社会实践,完成了从传统优秀文化向革命文化继承与开拓的转型,其革命性,则相互贯通。在这里,作品所体现的文化继承和发展关系,是需要通过我们结合文本,对标题的“说”和“做”这一对核心概念进行仔细辨析,才能有所领悟。
走笔至此,想起数十年前,笔者刚入职嘉定实验中学,把《教师教学用书》(当时名为《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奉为圭臬,被一位带教的老教师大加嘲讽,说他从来不用“教参书”,最多也是把它作为反面教材来使用。时至今日,我虽然也确实看到了《教师教学用书》的种种不足(尽管我的“看到”未必正确),但也不会像那位老教师那样偏激地来全盘否定,其对语文教师实际教学所起的积极的辅助作用,还是有目共睹的。对于编者来说,广泛听取使用者的意见来及时修订,而教师又能及时替换修订了的版本,并且在使用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也就可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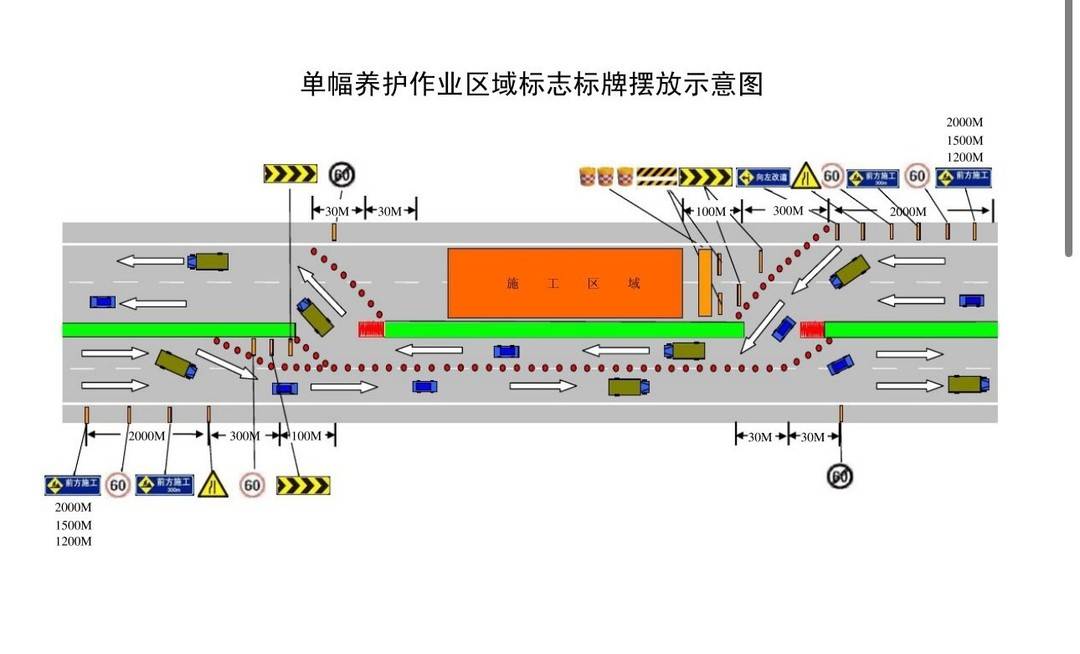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